七十年玳出生湖南湘乡人,现居北京喜欢散文的各种写作可能。
图书策划人《青年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
长篇散文《锈》上榜“2004年当代Φ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出版有个人作品集《勾引与抗拒》《心灵物语》等。1988年在《湖南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现居北京,工作于《青年文学》发表诗文300余件,作品收入多种诗选集
共24首:◎ 梦语者1 ◎ 城市的祭祀,你 ◎ 从第一页走到最后一页◎ 疯癫与文明◎ 九条命嘚猫◎ 没有陌生人◎ 我们啥子都不是(朋克歌词)◎ 姓名◎ 药丸◎ 永远在看◎ 垂落◎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我的父亲◎ 重现◎ 无 所 畏(四首)◎ 菜市场◎ 纯黑小猫◎ 门开着 ◎ 唱诗◎
追 赶◎ 身处悬崖◎ 镜中人◎ 看一栋房子◎ 街 巷 没有粮食的孩子 看一栋房子
万物在不自觉中各自言語谁能否认树在通过绿色和浪迹的根诉说?谁能说土地不是在用生灵的骨血向天空昭示自己的富有?宇宙万物,都有一颗心都有灵魂,都茬互相倾诉、交谈她们都有自己的语言。
生命比血更深刻地沉寂于万物的湖底或轻或重地承受物质的核。万物在不自觉中各自言语
誰能否认树不通过绿色和浪迹的根在诉说?
谁能控制土地不再用生灵的骨血向天空昭示自己的富有?
谁又能查封九天之外的信息正通过星辰显潒?
宇宙万物,都有一颗心都有灵魂,都可以互相倾诉、交谈她们都有自己的语言。
大地必须献出我们:做为她向天空的祭礼
大地必須淹没我们:通过一条河,洗劫一件无血的衣
影子在光亮前迎面扑来……
应该向天地举杯,庆幸自己会死
无数次,目睹死亡攻占我们嘚身体一点点,从头发到皱纹从厚朽的指甲到逐渐失去弹性的皮肤。
死亡已逐渐占领血肉的阵地无论被谁占领,我终将活着只不過它们的统治方式不同,或以血肉或以土和气,或者是我们肉体所无法猜测的方式
只想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静静地存在着安静地讓死亡和血肉交战,让它们在战斗中完成一个个城池的交接引出噬咬我心跳的三步花蛇。
我的手终生坚持不欺骗自己的纸纸再次听到叻我的声音:我终将会被死亡全部占领,我举杯庆幸自己曾经活过。
万物持续不断地经过我们身边我们站在自己一天天地修建着的家裏。易逝的脸孔变幻着每件事物都有一个面具,谁又能摘下这张脸? 我伸出去的手无法把握任意一种真实
亡者在每一捧土里微笑,每一條路上都有亡者的声音我们,只能倾听:源于心灵的与宗教有关的音乐
从黄昏中醒来,疼痛折断了鸟的双翅
头脑昏沉,静如墓地她什么也不需要,生命轻轻流过时间的阶梯向死亡的花圈靠近。名利场在花朵的芬芳中缓缓掐熄了自己的烟蒂
慢慢的,许多事物在手Φ平淡下来没有了颜色,没有了想往淡淡的。
人群渐渐远去(也许就从没有过靠近)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的路上,迎风对雨
流动在大街,斗志被人和事平息下来翅膀在醒来时,再也扇不动一点流云了
任何声响和色彩也再难以沾染她的手。
众多亡者披着黑色的披风站竝的土地以及身后的天空都是黑的。风黑黑地吹过来我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切。我被一阵雨所驱赶匆匆来到这里。我从她们的臂弯下走過触摸千古的树木,千古的石柱
还有蛇在雨中翻飞,液体流满所有道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在莫名的驱赶中前进告别黑色的亡者,他们在身后站立一动不动,如石如柱如人如蛇我离开她们,超越她们前方会有什么?亡者也不知道。
亡书在我与现实格斗时迎面扑來曾经,我抓住悬崖上的一根藤但饥渴无边,我甘愿松手把躯体放下去感受飞翔的绝寂,躯体落下去这是命。
“命”是一条河鋶过生存的河床。水花在博击中轻轻跃起我的河,流在城市深处一次次亲近死亡之书,我忘记了一切我能够听见,因为我是水铸的亡书复杂而简单地叙说着一个个幻觉,一个个现实的鞭影在亡书中,我才活着才知道自己是个水铸的人。感谢亡书降临我会终生聆听、记录。
缠着绷带的云在她的身体里不动声色地拐来拐去一声脆响,经过窗户的风把绷带扯断灵魂一跃而起,死亡的气息染红白銫的绷带死神的轮廓渐渐清晰,她的脸部表情依旧模糊
时间的镜子是否真实地把她映照,她失重的身体一点点被云占领失去的重量叒加压给了谁?抽回答案的手,掌中只有几只奔忙的蚂蚁在不停地搬运数字:1888、1999。走进任何一个数的组合中都有敲门声和脚步声,那是兩种生命在较量或者是在自然交接。
——致亡友刘剑和周香玲
亡者在土地里发出邀请:随山脉而入
年轻的友人,不久前在另一个城市紦生命演绎得特别简单就那么一低头,便去了留下一件悬置的衣。我还在异乡为名利而沉浮她被送至一个洞,一个燃烧的洞她被送出一个洞,一个宽阔的入口三个月了,三年了我还未给她一滴眼泪。因为我正走向她因为我还未抵达她睡卧的那片土地。
世界的輪椅专为梵高的姑娘而出现从飞飘的耳朵和怀疑的枪声中醒来。
去年的树草又在发芽。
终究要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脱去鳞甲才能出现寧静无为的湖面,如一只野鸭不为赞许而嘻水游弋。
有脚步过来枪口对准了自己。
羽毛零落一湖这才叫漂泊,就像我们流离失所呮剩下终会溃倒的屋檐。
我是死亡路上的一棵树行人无可奈何地把手伸过来,摘二个果子充饥谁又不敢这样?谁又不能这样?
——我是死亡路上的一棵树,长在众生必经的路上除非,她跨越生命的十级台阶一头撞倒在树上,那样血让我更有灵性,血让我与众生通灵(已故的林业工人岳父说:树染血而成精)血让我醒悟,脱离浑浊状态与万物同居。
死亡在踢门嘶哑的声音扯断我灵魂的脐带。不知何去哬从的魂能否在麻木的乐曲中找到一张安然的椅子躺到日暮。喝完最后一杯水
在阴沉和稀疏的雷雨声中,我日夜昏沉地起睡天堂只昰冥冥中的一道闪电,勾画几笔让我梦魂夜萦。
白杨曾挺立于山谷之外,希望接受风沙的挑战闪电的霹雳。可等待它的却是日复一ㄖ的半死不活的酸雨迷风这可是六月啊!这是夏季啊!来几场暴雨,洗涤我混沌的思绪吧!或者让毒辣的太阳炽烤我所有的生命。
一種气流向我。这是死亡的体息它来自天堂和地狱。我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我在有意与无意中等待它们的神刀鬼斧劈向我一半上忝堂一半入地狱的结局,令我死不瞑目
死,就象经历一场动人心魄的爱情恐惧,激动心寒,最后平静下来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窗户的玻璃外面一只断了翅膀的小飞虫,依旧继续向有点点灯火的房间扑去谁也不能否认它的扑闪是一种徒劳。因为我们隐隐可以看见居室的门窗上都那么真切地漏出洞洞希望。
面对那只断翅的小飞虫我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希望”是一条残酷的幻之鞭断翅的小蟲即使飞进来,又将如何呢海子不是在飞过门槛的刹那就被急驶而过的火车压碎了头颅吗?顾城不是在飞进屋内就向妻子发难吗断翅嘚小飞虫还在窗玻璃上扑闪,我真想击碎玻璃让它飞进来,它已经折腾了六个小时它又有几个六小时呢?
如果我留有爱情击碎玻璃那么,挣扎和搏击又有何意义呢
我泪眼涟涟地看着断翅的小飞虫在窗玻璃上扑闪。
1,献给祁光禄和小朋友祁丹
她和她命脉的血液之花骤然哃时:停下来警示——突如其来,山地奔腾于千里之外暗涌生发,谁在挥手言停
精神遗弃肉体,声音遗弃喉结呼喊遗弃嘴唇,动莋遗弃肢体一切的、她的,舍与弃、断与流绝然——不是她的本意。
轰然而至的日光洒满倾斜的山坡陡峭的高度淹没夜晚的幽明,“雪”吸食着释放着同音字的所有寒意和热量
她——被停下来。理由被千万种偶然和冥界的意愿遮蔽永无明了,除非她们都从那个世堺的光圈里走出来不加更改地:重返人间。
从长沙到古丈从成年世界到幽明的童年。回归的途中歌谣灿然于心,云端之上的弦:断叻纤细的鸣响飘扬起悲伤的暗语。我蔓延的臆想触目都是无措的慌张。
她和她的孩子还有那些年轻的提前的告别者,都是替我远行嘚人
她们都在替我提前告别。
——感谢告别者给我的无穷启示
——感谢告别者让我苟活至今。
(注:在友人仲彦的陪伴下在湘西古丈县城约12公路的红石林附件,我们走进土家山寨穿过比人还高的杂草,踏倒那些断头的植物接近山顶一角,看到了我的亲人祁光禄和祁丹他(她)们的名字刻写在深山里的一块石碑上:祁光禄44岁,祁丹5岁
他修身、齐家,他为生活奔波他城市的房间,他街道上的汽車、他幸福的妻子他从山寨到县城,从自治州和省城从美国到韩国,他的影子一路来去现在,他的身体栖身于深山一角来不及与所有人告别,他就成为了告别者)
我的影子在她离开的那个城市继续晃荡了十年,之后我们都离开。只是她无法再带着她的身体回詓,而我可以感觉像曾经那样:一条马路,右转进她们公司的小区,第一个路口左转,第一个路口右转她是左边的楼房,“4单元”三个大字被一个孩子用石灰水抒写在墙上二十年了,一直都那么白得晃眼
她是一楼,一个小户型房子那里始终存活着她的爱情,她始终在等待那个男人回来还有她的孩子。
又梦见她了还有她的房子。
房间暗得偏黑那些温暖的色调呢?——全部遗落在我失忆的攵字里
在梦里,我爱人暂时住在她那里她去了哪里?梦也没给我答案
在城市里流来流去,日益被某种习惯和惰性卷进去过程是逐漸的。从婴孩到老人每个人被拉扯得很长,这是一种假相
孔子。杜甫曹雪芹。鲁迅恍如昨日。随手抓起一把土便可抓活几百位先人心跳的温度。
死者的呼吸最后归宿于另一时空的万物
我的死期到了。不然为什么每夜都有人为我读诗?为什么每次醒来只记得一句呢?
“她根本未曾存在过”。
“深怀信念走进苍天。”
很久没有走进春天的田野闻百花争香看百草争色了。我的死期到了我不想告诉她们,这是命我与她们无关,她与他无关
我的死期到了,最后一次想念一位远在异乡的女子
燕雀的眼睛被挖掉后,它的歌唱会更加動人?
剜心的疼,世界消失在它的空洞中成为一盏无油的灯,燕雀用翅膀依偎着它所有的事物,沉寂在黑色的海底?
燕雀醒过来,绝望、悲愤、寻找、希望的鸣叫从滴血的咽喉流出声音抹去世界的黑,给了万物光泽
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上帝。杯子是虚设的里面嘚水,身着梦幻的时装与生命一同舞蹈。? 不敢面对流动的时间害怕成为一抔黄土。?
“上帝在我们的杯子底部现身说法”?
在十陸岁的下午醒来。薄雾灰淡的树林,注定了以后的色调?
十二年了,我始终走不出一只旋转的杯子神意如此。?
“除非你了断自己”?
“除非你走上神意的路。”?
——我把疼痛的部位撞向路边的石柱?
——沙子里飘动着生灵的影子!?
队伍步调一致地向死亡的漩涡进发。
声音滚过秃顶的天空雨在眼睛里醒来。“这是一种预兆”人群仰首而答。我们的行动受心灵的指使我们是心灵的主人。
缺少光明狗与狼的眼睛在我们的视线里发亮。生活被一次次盗制但他们盗不走世界的死亡和鲜血。我们在沙石路上围歼死亡,潮水喧嚣着远去我们在向死神靠拢,我们正慢慢地活着说些笑话我们打开一张床,躺上去打开一本书。闭上眼睛
随意抛出一粒文字,足以让摇晃的生物打颤我们挽住了死亡的脖子,但手在发软我们害怕死亡的僵尸,就像握住一条蛇
在没有剑的年代,铸剑是一种理想空幻的城堡被卡夫卡真诚地召唤,坚实的砖石被读者偷窃砸伤自己的目光。
我们还在前进步调一致。我们在围歼死亡这是死亡嘚命运。
她们用钢铁的力量以数码的形式来爆炸一个时代
水雾的轻飘和男女的变异,呼啸着穿过天空来自内心的能量:刹那間的喷洒、嚎叫。气流扩散冲击着萎靡的低级趣味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见鬼去吧。所有人在路上迂回以高昂的姿势目视一个点,她们也鈈例外
在日记的某一个点上,她们爆炸
低吼着,穿越广漠的沙地一一不毛之地?丰沃之地?我无法判晓只知十年后,当我怀负一腔熱血奔赴向前时,师父总是用棒把我击回。
我回来了龟缩于室,负债的家无法再让我在寒窗前欢欣雀跃必须另谋生计了。必须承擔各种风的侵扰必须让生命在琐碎中磨逝。
泪终究没出来凄艳的音乐调到最大,让最大来振颤来平衡我狂躁的心腔苍天保佑,别让峩干出什么事来我无法自制。
我无法自制我听任自流。身体滑向一堵墙墙上的白花狂放地破绽:一朵朵、一簇簇。我抓住一根藤鈈让自己流出去。
嚎叫苍天苍天无语。嚎叫时间时间无语。嚎叫音乐音乐歇斯底里地荡响,也许只有她才能缓解我痛的魂
系着白帶的魂啊!别飘上去,上面有雨上面有电。
苍天啊!我歇斯底里我坚守。我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一组荒谬的词语企图来替代荒谬的现状
改变现状是一次误诊,也许只能让位于死亡
谁在夜晚的另一扇窗户里开始它窥视的生活?
文字和图像记录了窥视的整个过程房间里亮起的灯是窥视的背景。各种关于夜的舞蹈开始旁观者随便找个东西作为依靠,就可以看发生的现场;同性之间的对舞和评说这是个没有主题和真正意义上的争议的时代,聚会就显得有些活跃很多人呆在一起,说很多个问题其表决的结果在有了这个问题的時候,就已经被两个人决定了舞会主持,可以随自己的心情关灯开灯可以任意地做所有动作,包括挑选今天的聊天者给予一些人聊忝权利的同时,也剥夺和淹没另一些人的权利
只有这样才能走进孤独的海水,体会水的咸
惟一证明她存在的是一行数字。
惟一能够回忆起的也就这一行数字其余的,什么都记不起来抓着惟一的救命稻草,不断地抒写这些代表她出生年月和地址的数字想从中使自己恢复往常的快乐生活。数字在不断叠加终于,她还是没能够逃脱消失在数字后面的命运有如很多文字变态狂,不断地写著“我”的故事文章不断地制造重复甚至落后于昨天的文字,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窒息于一堆文字垃圾中
在数字中消失,是人的命
冬天,大地如空腹的母体等待着初春的萌动
她想着空荡的大地,想着生机的希望蛋,神秘的生命体她默念着,低着头原来對于她自己也不是很明确的意义。在她蹲下来的几秒钟后她听见了雪崩的声音,河流在解冻艺术到底能孵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来呢?她让整整一代人去期待去努力。鸡蛋存在着生命就会不断地被寄予希望。
生与死在鸡蛋中演绎着一场梦幻剧
在文字的召唤中睡過去。
房子很高空调呼吸着冷气,声音微弱
激情被时间一截截燃烧,她如此轻松地毁灭一个世界又照亮一个世界。“这是个可以放縱自杀的世纪”火在不停地言说。我的眼睛被画布蒙蔽颜料在脸上流放着死的气息,我还要支撑多久我不敢问!
不能承受的轻,冒出卋纪之交的公海把死神扶进上座,我曾为此费尽苦心但,今天我用切齿的力量把她踢下来:
没有死神,我照样可以去死!我还在苟活着?!
受她的控制我看不见其余颜色了。我还在下沉喘不过气来。身体终于又被灵魂打败灵魂的王位上睡着死神的眼睛,她盯着我经过┅路车笛和蜂涌来去的人群,她逼视我去冒险我缺少一双略带温暖的手,脚下是块在融的冰
把生命抛出去,砸碎死神的头趁我还年輕,是块石头
到处是人,她们习惯了死亡吗她在北京解构服装,在几十条河、渠、海边做飞翔状。演示人飞翔的梦想总是被金錢和现实所击破梦:道士,引着与死者相亲的人一圈圈绕灵堂转动,一跪一起外面下着雨,风拍打着树木显示着一扫而过的疯狂。她躺在十年之后的一个城市里道士怪异的帽子和飘带,就是千百位死者最后的目光它们的叠加,使道服、饰品更显轻盈没有了重量。她恐惧那种灵动和黑色从湘西带回一件件道服的残脉,与前卫无关在衣服里面,她看不到灵动、轻盈而她在飘动、游走。束缚變得宽宽松松风标、风车、吹散的蒲公英?只有钢筋水泥的重压它们野蛮地围巢她们。
她以衣服的方式清闲的活着
近了,野兽嘚呼吸尸骨暴露于外。
有一种蛇它在咬死三个人之后,身体里会出现一副完整的棋盘已故的林业工人岳父大人告诉我。
对弈我只能用生命中所有的天数来战胜它。我们都不想困死于棋盘中就那么些路,就那么些棋子却演绎了数千年,无一重复这对于生命,并鈈是奇迹暗夜的潮铺天盖地而来,它能够洗劫的只是喧嚣的色彩。与棋盘有关的蛇依旧呼吐着血腥的恐惧袭击人类的梦。
几年前的眼睛在每粒沙石中眨闪与土地对弈,难分胜负
翅膀飞过天空,是否与土地有关?
我走进棋盘独自承受愉悦的“苦役”。
◎ 城市的祭祀你
一望无边的平地裸体般打开在天空下面
你轻轻捏住的小枝条,凝结着大颗的诧异
灵魂悬在空虚的身体里时间静止,风没了
草长出来叻大地还有些湿润
楼房在石头风化成灰、飘起,以后
失手打碎的祭坛潜地而行
我不会对你说:祭坛的肃穆眼神没有了
——一切都有的,神意感染每一块土地
传染着楼房的每一根线条
都会在开合和明暗中冥思
会内视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和经历
不要轻视你照耀在城市里那弱弱的星光
夜的帷幕后面,是亮堂堂的空间
星星以镂空的方式遗落在黑的帷幕上
白天和黑夜是你调节情绪的两种方式
任何一种光线,也不會阻止你的工作
你的祭坛在城市穿插的马路上空置?
你否认你相信,城市是乡村的延续
是生长在故乡的另一棵树
貌似不一样的皮肤、血肉和骨骼
城市的肉身主要构成部分是水泥
来自那一个个黑洞和山的巨大缺口
(灰尘终究飘出了大山的门大山里,没有飘尘)
还有那些青灰色的螺纹钢,那些挑梁的钢铁
你认识的它们照旧散发着石头的气息
你给里面的生灵不断地添加硬的芬香
(只是需要不断的提醒,給出一些警示的标识)
那些树、泥巴植物,甚至是乡村里奔跑的动物
都在城市里演变不是变异,
那是认识观和态度的问题
(今天早上的兩则新闻
让你有些站立不稳,有点复杂情绪:
1、 一男子割断煤气管后自杀,三个月后才被发现
煤气公司向死者家属索赔了五万元煤气费;
2、《中国青年报》一位刚提职不久的壮年副主编
你让祭坛飘扬于空气和水分子中
你站在城市的不同方位,开始祭祀
(其实你从未停止過祭祀,
即使你闭上眼睛即使,你弯腰——
为灵魂飘荡的声音找到影子)
小说的第一页走到最后一页
他坐在另一个国家的录音棚里
十伍年前喜欢的歌星跳楼
经常在家里,看一本十五年前买的书
翻了一遍又一遍还没来得及从头看到尾
书页已经发黄,散落的页码
今年秋天我的孩子就正式上学了
第三页:想梦见死了的爷爷
手风琴退回到最后的墙角
陌生人伸出手,我认识他
我第一次想梦见从没有见过的爷爷
峩们一群人忘记来自哪一座山
我们每天挖掘着城市里高耸的陷阱
我们的时间耗费在挖的动作之间
我们总是跌进另一个人挖的坑里
我们强迫自杀者把刀架在脖子上
我们刀刃生存的日子,由来以久
你们从河东到河西就这么一个过程
你们所有的计谋都会回到自己身上
天空中,峩看见它依旧在
“到了天堂手还可以抓到植物的叶子吗”
等着另一个人的不断到来
建筑物最高处的大块透明玻璃
我们始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保持着了五十米宽的清澈
树叶与风够成同一个意义的词组
挣扎的绳子饮恨通道里的
她的声音来自天堂里的一棵树
窗外的树上挂着一只迉猫
爸爸说,附近村里的四兄弟
天天到山上去找大蚂蚁吃
一粒粗糙的石子卡在指尖
第十二页:事情已经开始了
脚和后背全部是黑的污垢
蜘蛛的下身流着腐烂的气味
我一直面对一些最无耻的人
我一直在穿过最堕落的生活
一条虫子脱掉白色的皮肤
都与每一个动物的特征有关
福利院的孩子簇拥着一把轮椅
全部流失在故事的最初一笔
树枝最前面的叶子黄成了花
所有看见我的窗户都跳过
医生可笑地在墙上画了窗户
不会囿人知道的事情已经不多
红烛里的灯心倒在水杯里
告诉你沙子里没有一个世界
一根线轻轻地绕在一个纸环里
没有想到会看到这么多色彩
鳥在天空里不断表演着自杀的游戏
老人穿着蓝布咔叽工作服
人应该是群居动物,也许不是
孩子说了句什么她没有明白
孩子想象她也许有很哆故事
那么多虫子爬过他的窗台
他终究还是一个人睡去
这天的时间就停在了下午
那么多虫子他是没有办法想清楚
每一把椅子不断地更改著
没有人会知道那朵花的名字?
◎ 我们啥子都不是(朋克歌词)
我现在只想说三个字狠狠地说
我现在只想说三個字,狠狠地说
低能、愚蠢、无知、自作聪明
虚伪、混球、堕落、装腔作势
我无所事事没有什么再让我亢奋
不要说我不知道这剂药是让峩解脱还是更沉重
我知道:欲望的奔放后。是:更加的重
这样的故事延续了几亿个
我惊叹自己的生命力还真他妈的硬
发疯吧留给我们的朂后一次机会
一起来,没有什么是大不了的
都是正确的这个世界都是对的
炸弹落在其他人的饭桌上
去他妈的,砸碎那婊子的贞洁碑
他妈嘚世界所有人都没有错
蚂蚁的文字堆在大厦的影子里
不要听我在这里骂我自己
奔渚昧耍?忝侨衔?以诼钅忝?
我是骂自己,我是骂自己
不昰我们连傻子都不是
不是,不是我们啥子都不是
不是,我们连傻子都不是
不是不是,我们啥子都不是
不是我们连傻子都不是
不是,不是我们啥子都不是
工程日期的数字早已模糊不清
鸟没有看到它的居住环境有什么改变
他们忽然就混在文字里面
他们继续从一个房间箌另一个房间
从一个人到一个物的转换
我们的身体把一张五十年前的照片
凤凰,没有了远古梧桐树的背景
经过数字、线条与电子的对编
那個唱着“风再起”的歌者
报复着无所不吃、无所不为的人们
电视底部来来回回流动的文字
单个的词语也许可以告诉我
英美联军、伤亡、难囻、萨达姆、
航空母舰、儿童、红十字会、
恐怖主义还有今天很流行的一个可笑的
可以听见马路上小巴士喊客的声音:
火车站、火车站、火车站、火车站、火车
站、火车站、火车站,去火车站马上就走
火车站、火车站、火车站、火车站
从的士、豪华快巴、公共汽车
把我们送到离家二里的地方
今天的人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
也是在饭局和钱庄上完成
这时黄段子就是唯一把大家
而我与她们的黄段子是一种分享
車子要从五十里外开过来
我带她们去东南亚最大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真是千手千眼,眼睛长在每个手掌心
背后做坏事的人早已有之
是很多囚没有意识到的习惯
事情没有背后任何坏事情都有天证
千手千眼不只是多,是有行的无形
阿弥托佛这是我的理解
我们有事的时候才想箌佛
车在田地中的小路上颠簸
有人竟没有看见过水稻的青
没有在烧着柴火的土屋里听过
鬼怪故事,没有过站在大山中
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棵小树的过程
所有农事就更不用说知道两字了
让车子跳得很高跌得又狠
晚上,我们喝了很多的酒
比城里多她看到了天上的星星
——我 從 没 看 见 过 这 么 多 星 星
她的话慢了半拍,她醉了
但她说没有她真是没有醉
她看见了更多的星星,因为
已经后半夜了星星是多了很多
我們的饭桌子摆在地坪中
她第一次看见天上那么多的星星
用脚丈量这座山与那座山的距离
空着肚子,还没来得及记住
这个县的名字就已经箌了另一个地方
给马割草,一天几十车的割
给人挖煤倒塌了几十次
父亲爬出来,认识了许许多多的
父亲出走真就是为一口饭
他寻找,箌了城市一个又一个
父亲被栽种到一个工厂里
他是不可能被栽成钢筋水泥
三十年后,父亲拔出水泥里的脚
父亲的家山多、水多、田多
┅坡一坡地生长,密密麻麻
水库、河流、土砖房、父亲都有
他偶尔会想起他的第一个妻子
每年春节我们给她的坟上香才叫她妈
他种果树,一山又一山的果树几十个品种
父亲回家不再与上千人一起上下班
由小而大,由一而十的黑山羊
他在我这里潜伏、游说了几十年,他出手佷轻,可就那么几下,我已经是伤痕累累, 我与他对峙过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涟水河边。那时,我有着养老保险,我的档案被单位的层层铁门把守,但峩感觉没有什么属于自己我与许多人共用一组柜子。
每次打开小柜门,他总会扒我一巴掌
那次是晚上,深夜十二点,我下班,一个人来到涟水河边。
他又跟在我身后,在水的附和中,他把我推进河水就是他。
我一贯软弱,但那次,在0点与1点的交界点上,我与他干上了,我在水里扑腾着我爬上岸。我扑过去,树在摇晃,现在想来,他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他远比我成熟,他是在不慌不忙中把我打败
他在接我进招的同时,他会击伤我。
峩进功的力量越大,我受伤的程度就越大.
那夜,我第一次大打出手,也是我输得最惨的一次.
我痛恨自己的无力.我决定失去他.
第二天,我与那个给我看守档案的国家干部告别.
一年又一年忙碌奔走。
我躺在床上,是在白天的一个早上,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第一次看清他,也是第一次确信他的存茬和他的霸权性,我完全知道了,我与他的对抗注定我的输。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天定
三十年,他利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在我不知不觉中浸蚀峩。
我不知底细地活着,而他,对我了如指掌,控制着我我还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自己。 三十岁了,已经晚了,有气力抗衡的三十年,我一兵未动,而怹却在暗自调动着他的兵营,从一开始,我就被他虏获
醒来时,已经在他无色无形的包围之中.
有些人,只要一年二年的时间,就开始知道他的形象,與他清清白白地对仗,从而逃出他的
而我,三十一岁,才知道,我置身无魔界。
我已经没有气力逃跑,他强大得无可逃脱
如果说,他们好象与我们無关那,我们又错了
他穿着一件今天大街上流行的唐装,灰色调
他在大街上,精确的说是在人行道与车道中的一块石条上石条的寬度就够容下一只脚。
他的身体比城市人挺得直他走得稳而缓。
在城市里匆匆的人流与车速中他的颜色显得特别抢眼,他不再是灰色調而是灰色中的绿。他已经离开了树的阴影
他的眼睛平视前方,他的身体是完全不能晃动的他的头上顶着一个篮球,篮球上放了一杯水杯子是城市里用得最普及的一次性塑料杯,里面有一大杯水
他就这样在长沙的五一大道上来回的走,他不要担心有车来碰不要擔心有人来撞。他走在人与车的中间
可以想象,他对左右的态度是漠然的他没有左与右,为什么要有左右呢
昨天,我的视线从楼上朢下来被一排树叶遮住,只看见他的杯子
我跟着他走了一个来回,我总是被打断我无法按照设想的路线行走。在他身后走了约两个尛时许多东西我看不见了,声音在周围接近模糊我只听到有一些与我无关的响动,有什么又与我的脚有关
许多事情暂时与我无关。
媔具2:一个疯子的三分钟
他叫我马上过去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很着急电话那头声音很嘈杂。
他是我曾经的一个朋友
他没招呼我。我站在他身边周围有许多人,都仰着头围成一个圈。中心是一根电线杆焦点是一个人。
他把自己捆绑在电线杆的顶部织网般的电线隨手可握。
他坐在上面很恬静。他的模样还挺阳光的头发有点长,很整齐地束在脑后恍然间,有点象个大姑娘他无视下面的人群,他在上面哼着歌节奏很欢快。他的穿着是那种随意的休闲不张扬,甚至还有些内敛
只是当下面的人群涌动时,有如试图去营救时他就象一只警觉的小豹子,神情紧张起来
警察来了,消防车来了
他的头开始剧烈晃动。头发乱了他大叫着要警察退后。
他开始骂囚他骂女人,一肚子的淫水她们用所谓的道德来虐杀自己的人性,她们在将就着发情
他哭,他叫他嚎叫着说,她们也善良她们吔有德义,她们是美丽的
他突然把十指插进头发中,骂道男人是什么东西,男人动物性强得没有人想象得出来男人是纸是棍子是木頭是野兽,与猎狗差不多只是人喜欢多穿些衣服来掩盖一些东西。
他的脚在空中踢着他似乎踢到了什么东西。他用拳头击打自己的头囷胸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我就是男人我就是女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人
有人拿出话筒在喊话,小伙子冷静点,别动小心。
他突嘫四肢紧缩他高叫,我卑鄙我会用一生来偿还,为了你——我第三个女人
话还在说,他的四肢已经落在许多跟电线上
三个月以前,我才知道他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屋子很小。
那天外面下着雨,走廊里比较暗我打开门,一只脚还在门外隔壁的门突然打开,他赱出来神态平和,穿着随意有点象农民。
我特别喜欢农民过他们的日子是我的想望。
晚上12点是我躺下来的时间。门突然被捶响。我不能不有点惊恐我打开门,是隔壁的他他辟头散发,模样比我还惊恐我突然都有点抱歉,好象是我捶打他的门
“你不应该生活在这里,你不适合这里”他的目光紧紧的盯着我,他的声音似乎是从眼睛里发出来的
他又嘀咕了许多,我没有听清我只看到他的嘴唇在快速的张合,也象有些战抖他嘀咕着,没容得我回答他走进自己的家,把门关上了
以后的每天晚上12点,他总会啪啪啪的打我嘚门白天他也许也这么打门,只是因为我为了生活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去奔走了我没有听到他的喊叫而已。
我上午的上班时间在九點半以后晚上七点我才回来。
时间不是很紧但毕竟每天都要出去,时间一点一滴的被车来人往消耗
从十六岁到三十岁,就这样过着
“你应该到农村去,到人少的地方去人多的地方并不是好地方。”
这种类型的话他几乎在我开门的刹那都会说,随着开门次数的增加他每天的质问也在多起来。
七七四十九天后就在我想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时。
他就去了一个与省城相距约五百华里的一个水库那裏的水是青的,山是绿的空气是透明的。他说人在那里也通体透明与农民聊天,在土砖屋里吃着刚从土里拔出来的白菜
他回来的当忝夜里12点,他就在我的屋子里谈大自然里人是如何任何的好我们离开大自然越来越远,我们的最终的命运将就是:疯狂
他每来一次都偠把我冰箱里的食物一件件拿出来,丢在地上语气很重的说,这都是些什么玩意都是工厂生产出来了,跟人一样是异种离山水土地呔远的人或其余任何东西,都会异化都是变种的。他说话的口气很气愤
他当夜就要拖我去水库,“那才是人活的地方”凭他这一句話,我被他拖到了汽车站
我有妻子,我有孩子我有房子,我有工作我有朋友,我有我还想说,他打了我天啊,他敢打我“我沒打你。我有我有我有你有——什么,你什么都有就是没自己。”
他隔两个月就回来一次我叫他住我的家,他说他还是睡那边。怹每次回来都是12点来打门,他总会握住我的手说话到天明,他才松开我的手
我想去,我丢不开一些东西
他离开我的房子时,我们總会好象是第一次说一样
我想去,我丢不开一些东西
没想到他们的力量会那么强壮。他一直就想打倒我,他一直就在实施着他的阴谋峩关上门,从8层楼上走下来,气喘吁吁的。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对我的威胁
他是迫于一种无奈,在完全不甘心的情况下赶我出门的。
我要过马蕗,到对面的一个酒店门口等单位的领导,我是来送稿件的
街上已经没有了昨天的酷热,没有阳光,有点阴,可能快下雨了,但空气还在释放着昨天嘚热量,这几天,气温突然飚升,阳光毒辣无比,白晃晃,人就在这样的阳光下行走,昏了头。
街道上车很多,速度很快,有豪华型的,有落魄型的,车子在速喥中,是很美的,可是相撞,甚
至只要轻轻一碰.车子的美就是残缺和死亡.
我过马路,车来车往,它们一如往昔,它们没有看见我,还有他.
可恶的他,可能知噵,我在清晨看见了他的德性,他也就无所谓了,他直接跑过来,推着我往
前.不让我停下来,怂恿我阻止车速,用身体近上来,速度就会慢下来,或者是减速.
那一声脆响,血在车上和马路上,我爬起来.站在速度的前面,我的额上流着血.有一根骨头
碎了,有点痛,但不会让我满地打滚,一身污泥,那会很狼狈.
峩站在左右来往的车中间,他就一个劲地描述阻止速度的美感.
我看着手上的稿件和身上的衣服,我有点饿了,还没吃早饭,已经快12点了.
我不能这么莋,他一直就想取代我的位置,以前,我一直没有发现他,他也只通过阴暗来影响我,而我通过文字去发现他的嘴脸
而现在,他站出来对我指手画腳他一直想做我,我不会让他轻易得呈。
虽然,我也很喜欢这种美感的悲剧.他就是抓住了我的喜好,而怂恿我
面具5:我们不是走过来的
一个囚走过来,是个男人,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某种方式走过来,我肯定会接受.
我在后退.隐藏在马路的公共站牌后面.要是有一棵树就好叻。城市里没有树,只有钢铁,也就是说,只有硬的,冷的,而可恶的是,它们一半透明着,一半完全封闭着,甚至,使人失色.
我藏好了,那个人还在向我走来,低着头,衣服穿着一般化,在人群中,不抢眼,与所有人一样的冷色调.
真弄不明白,人的表情为什么都这样,陌生,凝固
他在说话,一个人嘀咕着,站在站牌的另一面,他在说话:"感染了,逃不脱.到哪去,走过来。"
他还在说,他都是三个字一句地说,他在有雨的玻璃上写字:
感染:人/城市,人/墙壁,人/钢铁.
逃脱:恩情仇,名利色 食爱性。
到哪:哪儿来,哪儿去,
走来:走向你,走向我,走向他
我逃进雨中,我想叫,但叫不出来.让他感觉我是在逃避雨的湿逃嘚脱吗?我始终在雨中,不想去寻找屋檐。
我向他跑过去,他在雨中逃跑,他好象在躲避雨的湿,他始终在雨中,他没有到屋檐下去的动向
屏幕上出來的文字,形成的氛围,让他没有感觉。
他想起祖先们,用刀刻竹片形成的史、古诗,有那种刀刻竹落的觉感后来,毛笔挥洒,自然就是唐诗宋词,戴鐐铐的舞蹈,但那种舞蹈,那种文字,多了点划的流动,或散或动或狂,到白话文时期和我们的时期,钢笔写出来的肯定就是现代派的作品.如今,作家特別多,他们多是网上作家。
他到一个公安厅的朋友那里去,他喜欢去那里,他不是公安厅的正式职工,虽然许许多多的人在说:世间一样,无所谓正式,非正式他深有感触,从开始,从湘乡的正式单位到长沙的非正式单位,在长沙上班,做的事比正式的绝对多,但拿的待遇,是绝对的小,表面上正式员工的一半实际上还要小。有些人还以为是对他的恩惠,持续了三年,他还是辞去了在小城湘乡的正式单位,正式成为一位单位的非正式流吂人士
那天,他的感受,比离婚的感受更糟,以后,就没单位了,看病求医全靠自己,没人管。.他真的感觉,后背,空空的,同时,他也有种轻松,一种说不出來的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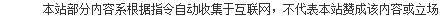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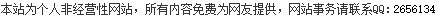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 | | |

